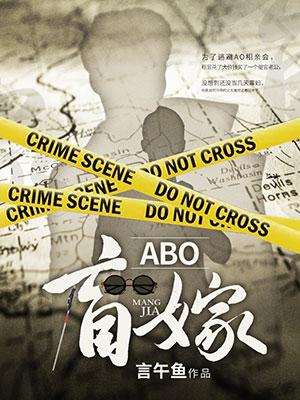洛城的深夜,除了夜车司机和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,所有人都已经倦鸟归巢,只除了肖默存。
床榻之上,一个清秀瘦削的青年正望眼欲穿、痛苦辗转。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四五岁年龄,皮肤苍白,眉头深蹙,满脸是汗。忍得太辛苦,他将嘴唇咬得破了皮,鲜血顺着裂口流下来,十指紧紧抓着身下濡湿的床单。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
难耐又无助的低吟从他紧咬的牙关中溢出,在寂静的房间里像钝刀磨骨,听得人寒毛倒竖。
他叫俞念,是个Beta,信息素味道是姜花,如果有谁的鼻子够灵的话。从晚十点到现在不过两个小时,他已经疼得冲到厕所吐了三回,直到胃里再也吐不出一点水。
三年前起,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像渴水的鱼一样,身体自动发出需要A10859信息素的信号。如果得不到满足,痛苦就会像烈焰一样烧得他体无完肤,整晚整晚阖不上眼。
比起Omega的发热期,这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折磨,与欲望丝毫无关。
电话再一次拨通,俞念脸贴着床单,哭腔浓重:“默存,你什么时候能到家……我、我好疼,快要撑不住了。”
眼前一阵阵发黑,身体出了层层虚汗,血液中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咬,让他忍不住想拿刀尖扎破自己的皮肤。
电话那头没人说话,沉默得令人绝望。就在他快要放弃时,大门突然砰一声响,脚步声不急不缓地朝卧室传来。
片刻后,一个高大的身影大步迈进屋内,冷睨了床上的俞念一眼,薄唇微动。
“怎么,又需要我的信息素了?”
“嗯……”俞念的双眼模糊一片,泪水朦胧中望着自己的Alpha,得救一般地挤出一个笑来。
“默存……”
他颤着右手拉开睡衣领口,露出自己脆弱的腺体。
“默存……咬我……”
体内可怕的痛苦折磨得他放弃了尊严,卑微地乞求眼前这个他爱了四年的男人疼惜他,快点给他的腺体一些痛,用这一点痛拯救所有的痛。
“默存……默存……求你了……”
见男人无动于衷,俞念在床上一点点往床畔爬去,身下的床单被他揪得皱成了一团。他仰起头,拼着最后一丝力气拽住男人的袖子不松手,口中一遍遍喊着男人的名字,凄厉又哀婉。
“默存……抱我……咬我……”
床边的男人却像是个看戏的陌生人。看得够了,然后才将俞念的指头一根根掰开,抽出手来用力掐住他的下巴,似乎终于肯给他一个痛快。嘴唇越凑越近,鼻息炙热灼烫,就在快要挨上腺体时却忽然反悔,将他从悬崖边狠狠摔了下去。
“俞念,你这样真让我恶心。”
男人甩开他的下巴,手指在衣服上擦拭了几下,似乎是嫌他脏了手。
“默存……”俞念目光涣散,睫毛上挂着一层疼出来的眼泪,低声哀求道,“你、你不肯再标记我了么?”
原本曲在床上的膝盖一撑而起,肖默存的声音冷若严霜:“我每标记你一次,心里的恶心就多一点,早就受够了,以后你是死是活都不要再找我。”
不,他的Alpha怎么能弃他而去?俞念心脏骤缩,几乎快要陷入昏迷。
“默存,你帮帮我……”
“默存”
“默存——!”
无声的尖喊之后,俞念从恶梦中惊醒,发现自己只是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,左耳的耳机还掉了出来。
窗子开着一条窄缝,午后暖热的微风徐徐吹来,撩起米棕色窗帘。
还好只是个梦,他捂着砰砰直跳的心脏,重重松了口气。梦是反的,肖默存还会在自己身边很久。
午休时间,周围的同事也都在休息。有的在眯午觉,有的在戴着耳机打游戏,没人注意到他的不对劲。他抽了张纸巾擦了擦自己额上的冷汗,动手翻了一页台历,接着一愣。
日有所思方有所梦,今天的确是需要临时标记的日子。